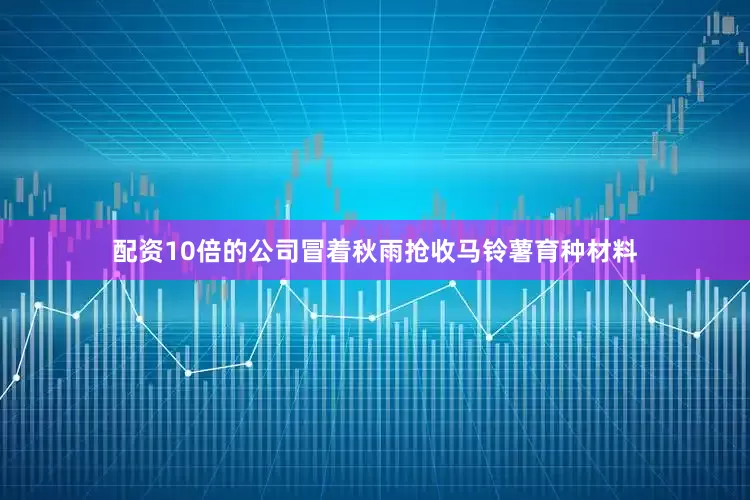日期:2025-11-05 05:28:33

1934年十月,受“左”倾教条主义者军事指挥失误之影响,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不幸失利,迫使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苏区,进行战略性的撤退。这次战略撤退是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进行的。与此同时,当时因“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而失去领导职位的毛泽东,尽管身处不利境地,仍竭尽所能,为长征的出发筹备了诸多必要事宜。

巩固南线苏区,强化统战。
为谈判陈济棠创造有利条件。
1934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对广昌发起了猛攻。博古与李德下令,中央红军主力应坚守广昌,并与之展开一场“决战”。为此,他们亲自奔赴广昌前线,而周恩来则留守后方,肩负起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自博古、李德离瑞金之后,毛泽东自二苏大会结束以来已闲置三月有余。在周恩来首肯之下,毛泽东携数位随员南下至会昌,对该地区进行视察并指导工作。抵达会昌后,毛泽东基于深入的调查研究,协助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等领导,制定了南线的作战策略与部署。他针对南线的局势进行了细致分析,强调需正确处理“打”与“和”的关系,指出和平局面需通过巧妙的战斗策略来赢得:“我们不能照搬那些书本先生们坐在城市高楼中设计出的洋方法,诸如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的战术,这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战斗力,消灭敌人,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避免无谓的消耗战。”他进一步指示,应将主力部队撤回,采用小部队的游击战与带有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引导敌人深入我方阵地;同时,还需对陈济棠部队及敌占区的人民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宣扬抗日救国、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理念。
毛泽东的这些言论,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导方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为粤赣省的党政军干部在开展南线反“围剿”斗争中指明了正确的道路。南线的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陈济棠多次加入了反蒋的阵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之后,将陈济棠封为南路军总司令,试图将他拉入战场,以期在粤军与红军交战的过程中削弱其实力,进而趁虚而入广东境内,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陈济棠显然洞悉了蒋介石的野心,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进攻赣南红军的态度显得消极。
“此前红军向粤赣边发展的策略,不仅客观上助长了蒋介石对两广的打压,亦符合其心愿,但此举无疑会迅速激发两广的共军行动。”“我们不应如此愚昧。”果然,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后,陈济棠和李宗仁趁蒋介石主力深陷江西苏区之际,于9月初起兵进军湖南。针对这一局势,蒋介石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调兵遣将,驻防赣粤边区,以阻止叛军扩张”。蒋介石军队撤退后,红一方面军先后在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等地展开战斗,成功击退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1934年6月的初期,毛泽东莅临会昌站塘的李官山,对红二十二师进行实地考察。归途中至文武坝,毛泽东特意强调,必须充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对刘晓与何长工说:“我们应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借助敌方内部纷争,壮大我方力量。我们不仅要坚守‘国门’,更应巧妙运用反动派间的分歧,深化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要紧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建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另一方面,可增派化装小队,潜入陈济棠辖区,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重要性,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抽调筠门岭一带部队进行整训,缓解前线紧张局势,同时积聚我军力量,以应对各种变数。”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南线红军在军事上采取主动、有计划地打击,既未消灭陈济棠的主力,又让陈济棠意识到红军并非易与之辈。同时,陈济棠亦认识到,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阻止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的关键力量。他既惧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入粤,又担忧红军乘机反击。因此,在占领筠门岭后,陈济棠采取了“外战内和”、“明攻暗和”的策略:一方面声称要与红军交战,另一方面又秘密派遣高级参谋杨幼敏前往筠门岭,与红军进行试探性谈判,寻求停止敌对行动。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送至驻会昌的红军部队。双方的这种互动,为后续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刻,中革军委计划将红七军团调往南线,意图夺回筠门岭。此举固然削弱了东线红军的战力,却也打破了南线与陈济棠之间的缓和态势,进一步激化了红军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对南线相对稳定的局势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毛泽东对此持反对意见。经过与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深入研讨,毛泽东于6月22日致信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南线的实际情况,指出:“敌人虽有意占领南坑、站塘,但仍保持谨慎态度”“判断敌情将逐渐演变,而非突变”,并建议红七军团不宜南调,建议军团长寻淮洲暂留瑞金待命。[4]周恩来采纳了这一建议。
总结而言,毛泽东抵达中央苏区南部战线后,巧妙运用正确策略,通过战斗推动和平,使得陈济棠深刻意识到红军与粤军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进而稳固了南部战线的局势。此举为长征出发前的双方谈判奠定了基础,促成了包括相互借道在内的五项协定的顺利达成,为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牵制敌人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赢得了宝贵时间。
积极争取张闻天的支持,以增强对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势力的力量。
张闻天,作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以及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出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其在党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上海的白区工作时期,他撰写了若干篇探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文章。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负面影响。例如,1932年11月3日,他在《斗争》杂志第30期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中,对当时左翼文艺批评家在“文艺自由辩论”和“文艺大众化”议题上显现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小资产阶级文学家是左翼文化的盟友,应对他们进行说服和争取,并坚持执行“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与博古之间的分歧逐渐加剧。针对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博古将其视为仅仅是宣传的号召,适用于下层士兵和广大工农群众;而张闻天则认为,这三个条件不仅是宣传的号召,也是行动的指南,同样适用于上层军官。[5]福建事变爆发后,张闻天主张在军事上积极配合。[6]然而,博古并未采纳他的建议。广昌战役结束后,张闻天批评说,与敌人硬拼导致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不正确的。博古则反唇相讥,指责张闻天持有类似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的机会主义思想。[7]这标志着张闻天与博古之间首次公开且激烈的冲突。这些意见上的分歧,使得博古与张闻天的关系愈发疏远,张闻天逐渐被边缘化,陷入无权的境地。对博古的行为,张闻天也日益感到不满。
1934年8月下旬,随着国民党军队持续向中央苏区核心区域进逼,其飞机对瑞金沙洲坝展开频繁轰炸。在此背景下,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革军委迁至瑞金西部的梅坑办公。张闻天将住所迁至瑞金城西约20公里的云石山,云石古寺内。毛泽东亦因养病而迁居于此。两人同处一地,频繁交流。长征前夕,毛泽东与张闻天在云石古寺前黄槲树下石凳上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张闻天毫无保留地与毛泽东分享了对博古的看法。张闻天回忆道:“自那以后,我与泽东同志的关系日益亲密。”
“他(毛泽东)建议我与他和王稼祥同志同住一地——从而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中央队’的三人集团,为遵义会议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赣南省进行视察,此举有力地保障了中央红军主力能够在于都顺利集结并踏上征程。
1934年秋季之初,中央苏区的局势急转直下,东、北两线相继失守,西线亦愈发严峻。面对战局的不利态势,毛泽东焦虑万分,遂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前往赣南省进行实地考察的请求,并获得了批准。同年9月中旬,他率领秘书、医生及警卫人员抵达了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以及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信丰河下游自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至大田一线十里以内,近日常有敌小队渡河骚扰,但近一周未见敌军活动。”电报最后强调:“于都、登贤全境目前尚未实施赤色戒严,敌特活动自由。目前正紧急在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巡逻和反间谍措施。”此电报对中共中央决定从于都方向突围长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毛泽东积极推动于都县开展扩红运动,旨在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储备兵员。9月1日,中央组织局和总动员武装部联合发布动员令,要求在9月27日前征集3万名青壮年加入红军。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县活动分子的紧急会议,即便疟疾初愈也毅然出席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反“围剿”战局的严峻性,激励大家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克服重重困难,确保完成扩红任务。毛泽东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与会人员的士气。次日,各区纷纷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进行再动员。于都县的扩红运动因此迅速取得突破。当中央红军主力转移之际,各军团共吸纳了9700名新兵,其中仅于都县在9月份的扩红人数便占到了总数的八分之一。
组建游击队以牵制敌人;努力提升生产效率,为前线提供支援;手工业应服务于农业与革命战争;对阶级敌人实行严格管控;干部需关心群众生活,并注意改进工作方法;对存在的缺点与错误,干部应自觉向群众检讨,并经常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他还接见了于都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参与生产,支持前线,并勉励亲属在前线英勇奋战。由此,广大民众、各级干部及红军家属明确了工作方向,为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切勿因红军主力撤离而认为革命已经失败,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困难,要看到革命道路的曲折与光明,坚信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必将到来。他强调,广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要丧失胜利的信心。
即便在遭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斥,被迫离开红军指挥职位时,毛泽东依然对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启动做出了关键贡献。以下是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几个原因:首先,他拥有强烈的革命使命感。即便身处逆境,毛泽东依旧牢记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尽力在所能及的范围内工作,以尽可能弥补“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害。其次,无论在粤赣省还是赣南省,毛泽东始终以调查研究和深入分析问题为起点,寻找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方案。他的这种工作方法对苏区各级干部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了工作的有效进行。第三,毛泽东始终将紧密联系群众作为工作的核心。他关心群众生活,尊重群众权益,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视他为亲人,对他坦诚相待,这使他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第四,他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始终强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视察中央苏区南线时,他指导粤赣省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通过斗争促和,缓解了红军与陈济棠的关系,稳定了南线局势,为日后与陈济棠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

配资门户网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十大炒股杠杆平台排行榜在八强赛和半决赛中两次通过互罚点球晋级
- 下一篇:没有了